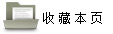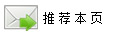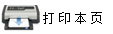压力是一种无形的怪物,是无休无止的担心和忧虑,工作的辛苦、身体的疲惫与它相比都微不足道。由于我工作的不稳定性,我没有一天能暂时逃脱掉压力的吞噬,每天入睡前都在着急地想,如果明天没有工作,这个星期就不能交给斯考特足够的钱,他就会马上去领救济,所有的这些辛苦就终将是白费……在这方面斯考特没有表示出任何体谅的态度,没有说过一句安慰的话。他让我坚信如果今天我拿不出足够的钱,或者是由于什么小事惹得他不高兴了,明天他就会去找政府。
以前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过看人脸色的生活,几次看见斯考特那副安然自得的样子,我的心里总是冒出一股火来,对自己说,老子不干了,签证不要了,什么大英帝国,去你的吧!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竟然一直忍了下来。这一点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这一张签证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要在这里过着这样的日子?问来问去没有答案。
我的乐队这时已经有了相当的起色,被一位有名的乐评人看中以后在报纸和电台大做宣传,也签下了与唱片公司和经纪人公司的合约,出版单曲以后开始在伦敦和其他城市小有名气。或许是东方女孩对于这里的观众来说既新鲜又神秘,每次演出都会出现疯狂的场面,造成一阵小小的轰动。但我们的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每个成员都有一份跟音乐完全无关的工作来养活自己,这在伦敦的音乐圈里是很普遍的事情。我的生活仿佛被分割成毫无关联的三个部分,由我扮演着截然不同的三个角色:舞台上傲视一切的艺人,白天挥汗如雨、没有姓名的打工者,还有从前生活中那个真实却已经遥远的我。
我的乐队曾经应邀参加拍摄后来去戛纳参展的电影《冷鱼》(ColdFish)。那一天我穿着一件VivianWestwood设计的上衣,站在舞台上辉煌耀眼,几乎震慑了台下所有的工作人员,赞美和欣赏的目光不时向我投来。最后一组镜头拍完是早上六点,导演和摄像把我亲自送上车,握着我的手说一定要和我再度合作。一夜没睡的我匆匆回到家里,换上工作服,立刻坐公共汽车去医院开始一天的工作。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两种身份的突然变换像是幻觉,但它却是我无法逃避的现实生活。
相关咨询请拨打400 666 1553(中国)0203 206 1211(
英国) 或发邮件到china@peinternational.co.uk(中国)enquiry@peinternational.co.uk (
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