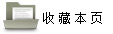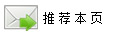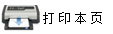2004年夏天,我扛着大包小包,从Loughborough搬到了伦敦,准备继续攻读我的第二学位。住在喧嚷的环境,拥有咫尺可近的繁华,这正是我Loughborough乡下读传媒时所翘首以盼的。Loughborough是一座宁静的大学城,却大而不当,买包方便面也要步行半个钟头,这让人觉得很烦。城镇中心也朴素简陋,摈弃了所有让人糜烂和堕落的因素,十分适合闭关修道。而我住在绿树掩映,松鼠出没的乡下,却不觉得这寂静是多么可喜,反倒时时盼望着伦敦的繁嚣。
伦敦果然是如我所愿的景象,满街各色人等,把10米宽的大道挤得水泄不通。华灯初上时更是灯红酒绿,光怪陆离。可俺知道,没钱说什么都他妈的是扯蛋。一天3小时的零工只供得起吃住,为了交学费,我开始在一家中餐馆打黑工。所谓“黑工”,就是每周工作 时间累计超过20小时。我每周干6天,下午5点开工,深夜12点收工,原则上共计42小时。
好在餐馆安排住宿,就在餐馆楼上一个6平米小屋。房间很简陋,一张床,一个破茶几,暗红的地毯显得脏兮兮。窗栓坏了关不上,一个大洞足够两个壮汉并排着走进来。探头一看,楼下尽是些体魄健朗的黑人,心里直发毛。后来只好挂上窗帘,终日紧闭,自欺欺人,竟也睡得香甜。
Johnny是俺的房东,也是餐馆的主人。15年前他揣着200英镑和一兜梦想来到这片土地,他刷过盘子,做过厨子,送过外卖,如今他是两家中国餐馆和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板。在无数做着出国梦的人们中,他的事迹被反复传诵并无限放大。他把我引荐给这里的老板James,并嘱咐我好好干。
我们的餐馆叫Great Wall,工作 人员只有老板,大厨,送餐的小陈和我,凑成了一个简单的四口之家。吃饭时我们各占桌子的一角,显得合理又和谐。初到餐馆时,我是餐馆的“楼面”,说白了就是服务员,负责接电话,记菜单,陪客人说话,总之做一切说英语的事儿,周末生意忙时还要进厨房打打包。
打从我当上传说中的“楼面”之后,摆在我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背菜名,280个菜名。菜式乍一看有280道,其实就那么几样颠三倒四换着名儿糊弄鬼子。价格倒是贼贵,如扬州炒饭一盒3镑(45RMB),咕咾肉一份4镑(60RMB)。好在背东西是我的强项,于是我头天上班当晚,就手握“红宝书”,前后左右踱步,嘴里还哼哼唧唧念念有词。那天晚上都不记得是怎么睡着的,总之梦里尽是些chicken curry, special fried rice, BBQ Spare ribs的单词在乱飞,醒来时手里还紧攥着一张菜单。
然而记清楚菜名仅是万里长征迈出关键第一步,第二步竟然是学习写错别字!比如:“鸡”写成“介”,“鸭”写成 “甲”,“虾”写成“下”,“猪” 写成“朱”等等不胜枚举。因为楼面所使用语言的对象只有一个——大厨。凡是大厨看不懂的,统统是烂语言,大厨看得懂的,才是好语言。错别字也不例外。于是在客人下单时,我不得不经历3个痛苦阶段:把听到的英语在大脑里翻译成汉语;把翻译后的汉字写法转换成错别字;把菜价写到菜名的正右边。其中以第3条最崩溃,几乎一个月后我才真正将280道菜价烂熟于心。
偶尔遇到一两个变态的顾客,等你好容易记下全部菜名菜价地址电话,正要撕单送厨房,他冷不丁来一句:“So,what’s the total?”此时你只有忍住全部的厌烦厌倦情绪,拿出中国传统算术的精遂来,飞快地加减乘除,并告诉他总价。若是不幸遇上脑髓里有些贵恙的主顾,没准会在你下单N久后,拨一通电话过来,用极其轻松的口吻说:“Oh,my darling,could I change my order?”这时,我只有用脖子夹着电话继续寒喧,左手招呼柜台前等待的顾客稍安勿燥,右手在一堆菜单里大海捞针一样去拣他的副单,核对无误后再修改,再招手示意小陈出来递单,然后嘴里说着Thank you心里想着Fuck you挂了电话。
头一个月,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生怕自己记错菜名,路名,门牌号。菜名错了,厨房需要重做不算,餐送到了客人还会打电话过来骂人。粗口是我一个人受用了,餐总是要重送的。若是遇上大雨天甚至是大雪天,此时的心情,只恨不得砍自己一刀的。如此几次以后,身心俱伤。
后来,工作 上手后,我逐渐能够从客人的口音里将熟客一一辨别,不等他们自报家门就抢先一步说出来,哄得他们心里那个美啊,从电话里都能听出喜上眉梢的模样。我同样可以从生客的语调里辨别出他们的肤色国藉,英国 本土白人,欧洲白人,本地生黑人,黑人移民,本地生印度人,印度移民……当然,还有中国人。正确率90%以上。我还学会了站油锅,炸各式各样的小吃;我学会了摆设冷盘、打包,还能在人手不足时炒饭。我会从容不迫地下单,我会在客人耍无赖时凶巴巴地说:“You idiot! Pay the bill as soon as possible, or I will report to the police!!”,这样的吓唬居然也很奏效。生意稍微好时,连上厕所的空隙也没有,这头刚蹲下那头电话又响个没完,一边提裤子一边就往柜台冲。厨房里的男人们也各忙各的,压根没工夫瞧我这个邋遢女子。我就如此在伦敦不由自主地模糊了性别。
只有在每个周六发银子时,我数着手里厚厚的一沓钞票,想到自己的学费有了着落,才高兴起来。第一周工资整整180镑子,被我用来购置家具。一个帆布大衣柜,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全部是从Argos网上买的便宜货。看着满满一屋子自己挣来的家具,很有成就感。得意之余,我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切就位,再拉上一条宽带,冲一杯速溶雀巢,想象自己住进了希尔顿饭店。虽然我吝啬得舍不得花一镑坐公车,但桌上一束“价值不菲”的鲜花却常换常新。鄙人时常自慰:俺虽穷,无背景,可比酷玩浪漫在上帝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在物质极度匮乏的那个夏季,鄙人的身体在沦陷,灵魂在高飞。
然而,餐馆生意好景不长,9月天气渐凉后,餐馆的生意有如悬崖上推下的一块巨石,颠颠撞撞的下滑。老板James一脸愁苦,拍着我的肩膀说:“生意再上不去,就该出去派单了。”
分发菜单,俗称派单,这是中国餐馆由于恶性竞争而萌芽的一项折磨人的新业务。说白了就是把印有电话号码的菜单挨家挨户的塞进信箱里,以达到广而告知的效果。这一举动彻底宣告了“酒香不怕巷子深”时代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现代信息广告时代的到来。
据Johnny回忆说,10年前分发菜单的傻冒很是寥寥,他偶尔出去派几天菜单,周末就会忙到连电话都不敢接。我和老板听了又是惊羡,又不由要感叹:那该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啊!多想回到那时候当傻冒啊!
没办法,我们注定遭遇不了那样的好年景,只好乖乖地派单去。我和老板一人脖子上挂一只包,包里是几百份菜单,晃晃悠悠地穿梭在伦敦南部小镇的住宅区。轻轻地推开每一扇院门,走进,至大门前,左手把信箱推开一条缝, 右手把菜单对折以增加硬度,塞进,成功,收右手,缩左手,走出,最后关院子的门。这一系列的动作看似白痴,其实大有讲究,每天重复性的执行之后也衍生出许多悲剧。下面举几个我曾亲历的例子——
凶悍型主人。派单的时候他/她正好要出门而不幸撞见。轻者会激动地大骂:“我毕生最讨厌中国菜单和pizza菜单……”(此处省略粗话100字)。往往这时候,英语听力会忽然出奇的好。重者会把菜单拣起来(如果你不幸已经投了),直接甩在你脸上或者朝你身体的某个部位抛来,并附加f,s 开头的单词n个。此类人多为女性,如有男性出现,表现形式尤为变态。
劣质的信箱。有的人家使用的信箱异常牢固,怎么都掰不开口。好容易使上吃奶的力气,塞进一张菜单,还没来得及抽回左手,喀嚓……左手食指被夹住,撕掉一大块手皮。后来我一直戴手套,还好后来一直是冬天。
让人无处可逃的狗。狗是英国 人民喜爱的宠物。几乎家家养狗,且不止一只。幸运的时候:菜单才塞进去一半,忽然听见一阵疯狂的狗吠,伴随着奔驰的脚步声,听声音判断数量在两头以上,我们只得落荒而逃,并庆幸无损伤。稍微倒霉一点的是:没有狗吠声,放心塞菜单,不料忽然手指一痛,原来被狗从里面咬了一口,轻微肉体损伤。比较倒霉的是:见一狗伏于床,似寐,于是放心要塞,猛然抬头只见快两米高的另一巨狗正趴在玻璃门上与你对视……全身血压往头顶冲,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严重精神创伤。
容易损坏的门。正要推开院子门进去,发现门是坏的。正要惊讶,主人已变戏法般地出现在面前,冷笑地看着你,一脸得意,仿佛说:“小样,赔门吧。”当即吐血。
人生何处不迷路。走到一个分岔口,分头行动。等一条街道分完回头一看,妈呀!人都哪去了?没带手机,没带钱。走啊走啊,越走越远。问路,答曰:坐两站就到了。我晕,我有钱坐车我还问路干嘛!绕一圈走到鼻塌嘴歪后终于回家。卧床不起。
厌烦的时候,我会很阿Q地安慰自己,出来派单既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减肥,同时创造经济效益。况且年轻人经历些挫折有利于看清资本主义社会人剥削人的罪恶本质。然而每天黄昏时,我挂着空荡荡的包,一个人走在伦敦的小巷里,看见放学的孩子簇拥着一起回家,看见一张张兴奋的脸从身旁一一滑过,用一种听不太真切的语言细细碎碎地交谈,心里就会落寞起来,一时间竟然忘了身在何方。
这里就是伦敦。这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教堂,这里有欧洲最密集的博物馆,这里有最具中世纪韵味的街道,这里还有百万个大商场,近千万人口。这里是我工作 生活学习的地方。我每天穿梭于伦敦的大街小巷,听街上的车声人声,教堂的钟声,街头艺人的琴声。我知道我身处于最热闹繁华的伦敦,我已在多愁善感中历练了许多岁月,然而这一刻我一个人,在人群中,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偶尔挪挪脖子上的包,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忧伤的味道。
相关咨询请拨打400 666 1553(中国)0203 206 1211(
英国 ) 或发邮件到china@peinternational.co.uk(中国)enquiry@peinternational.co.uk (
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