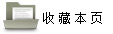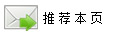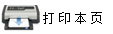现在想来奇怪的是,成语里那个比较抽象的“苛”字当时似乎已经在《苛政猛于虎》的课文里学到,“捐”字在我印象中也已经不陌生了。
纵使我的记忆有偏差,“税”字怎么读,做何解,在我的教育里也出现得比较晚,而且绝对是个贬义词:税是旧社会的东西,人民解放了,就不用为交税发愁了。
至于当时的课本中如何说明国家机构以及教育、卫生和国防之类开支的来源,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而我自己意识到那些展现农民高高兴兴交公粮的宣传画和新闻纪录片里的公粮不外就是收税,知道农民当时为中国经济的原始积累做过巨大牺牲,恐怕也是后来的事情。
所得税
第一次听说所得税,我倒是记忆深刻。
当时有个去中国的美国人来我们家做客,他得知中国没有所得税,觉得实在太幸福了。
等他听了我和哥哥们在工厂里当学徒工领取的工资水平之后,羡慕感倒是打了一点折扣。
那时候,三年学徒在开头一年每个月拿16.32元,之后晋升到19.32元,而出师以后的头几年也只有三十几块钱工资。
这虽然比当时农民的日子舒服一些,但十个月的全部收入才够买一辆自行车的钱,在那位客人眼中不具太大魅力。
在1960年代的宣传画中,交公粮是可喜的事情。后来有统计说中国农民在那个年代为国家建设的原始积累交公粮的奉献相当于数千亿元税收,怕是并不那么轻松。
退税
我自己第一次支付所得税,是20岁离开中国,一个人去澳大利亚闯天下的时候。当时我先后在超市、工地、旅馆和铁路上打过工,每处发薪时都在工资单上列明了扣除的所得税,让我不无惋惜。
不过后来发现,澳大利亚税制也有一些可爱之处。
首先,花钱受教育的开销有一定的免税额。我当时正琢磨学电影,买了个小小的摄影机到处拍,咨询后发现这可以算做学习设备,连同买胶片和冲洗胶片的钱全都可以算做教育投资。
这一来本已扣除的所得税到财政年底退了几百澳元。
澳大利亚的财政年度是从每年7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我决定要去欧洲恰好选择在年底离开,这样一来,在澳大利亚半年的收入便作为全年收入,这样重新计算,工资低了,已经扣除的所得税就要退还一部分。
我到了英国之后发现,一张澳大利亚政府的退税支票正等着我,一下化解了几个月的旅游导致的财政困境,增加了我对澳大利亚的美好记忆。
倒贴
在英国工作、学习了几年,我决定迁居德国时回想起这条经验,也选择在财政年中间的时候离开,以求再享退税的优势。只可惜那时候做学生收入无几,退税也没有多少。
到了柏林之后,我发现上学之余在剧院里跑龙套,搬道具挣到的钱虽然将将突破纳税的起点,在工资单上显示扣除了一小笔税。但是下面紧接着又有一栏,却显示政府退给我了大约相仿,有时甚至稍大的一笔钱。
起初我不想打草惊蛇,便没有细问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得知那时候的西德政府为了鼓励人到四面都被东德环抱的西柏林去生活,设了一个补贴,给工资附加8%。
虽然难说这对改善当时的生活有多么轰动的效益,但它的精神抚育效果显然不错,让我至今未忘。
漏洞
住在当时的西柏林还有一项税务方面的好处,那就是西柏林的地铁系统当中有一个柏林墙出现之前就存在的老站,位于东柏林地下。这是东德政府管辖的地盘,下车的话到了路面那层有进出东柏林的边界关卡。不过,下面的站台那一层却是西柏林地铁乘客专用的站台。
东德人在这个站台上设了免税店,经营烟酒和礼品商店,商品既无关税也无增值税,价格还不到西柏林市面的一半。
可想而知,不少人当时都去沾光,我也不例外。事隔多年我才听说西柏林政府当时有申报并收缴关税的规定,只是无人监管,让乘客们钻了漏洞。
挨罚
回到英国正经开始工作以后,我自然躲不过交税了。
不过到这时我即便不认同每届政府的征税模式和所有的开销,也早已接受了纳税的不可避免性,也接受了交税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然而前些年我还是挨了税务部门一棒,被罚了100镑。这不为别的,而就是因为例行的年度所得税报税表晚交了几天。
我愤愤不平,但回想到小学那篇《苛政猛于虎》,觉得和孔子见到的那位死了丈夫又死了儿子的老太太相比,我还是幸运儿,便忍气吞声地寄去了那笔罚款。